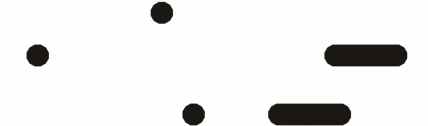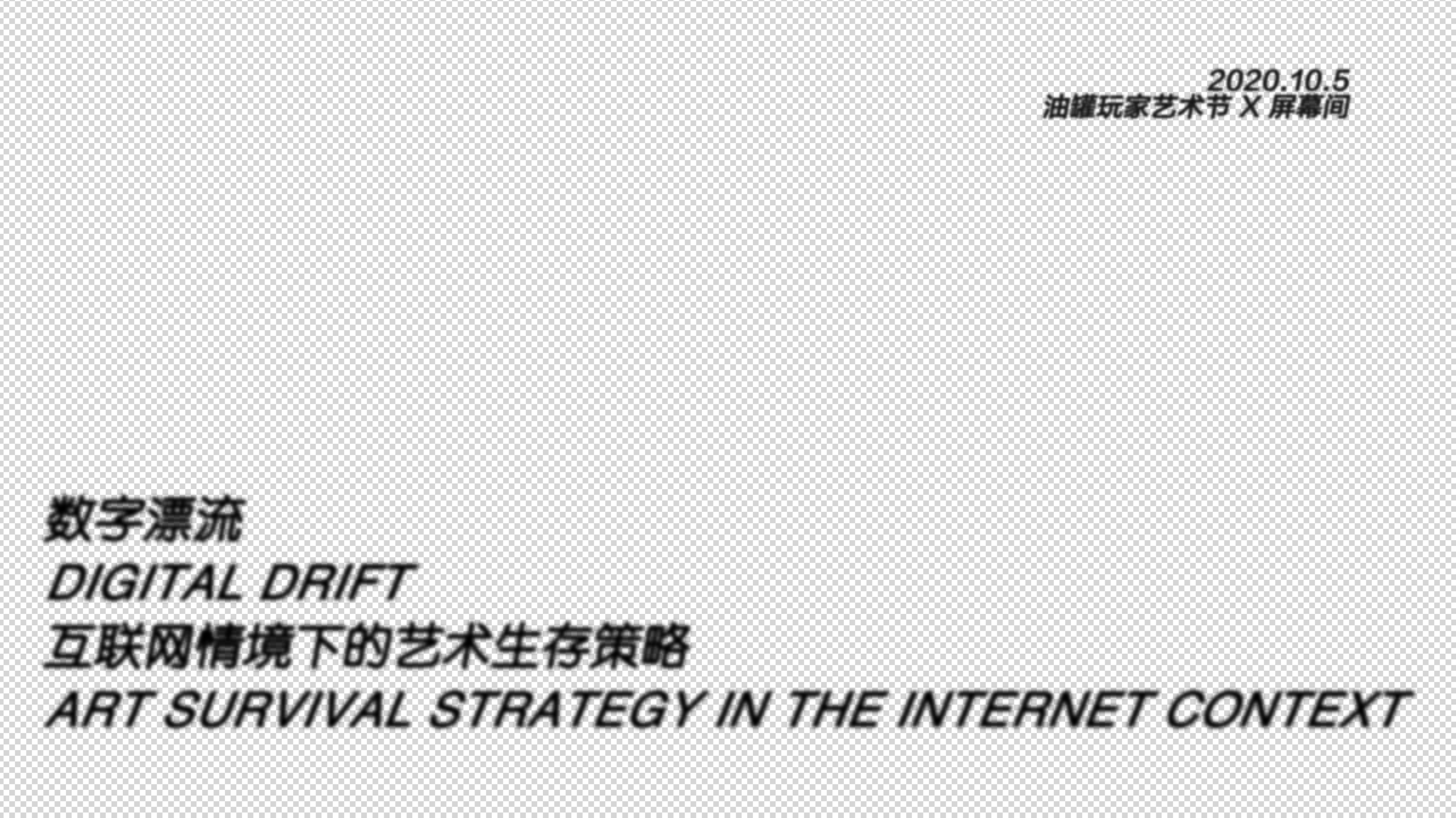

话题1. 对艺术家身份的讨论 & 对互联网语境的回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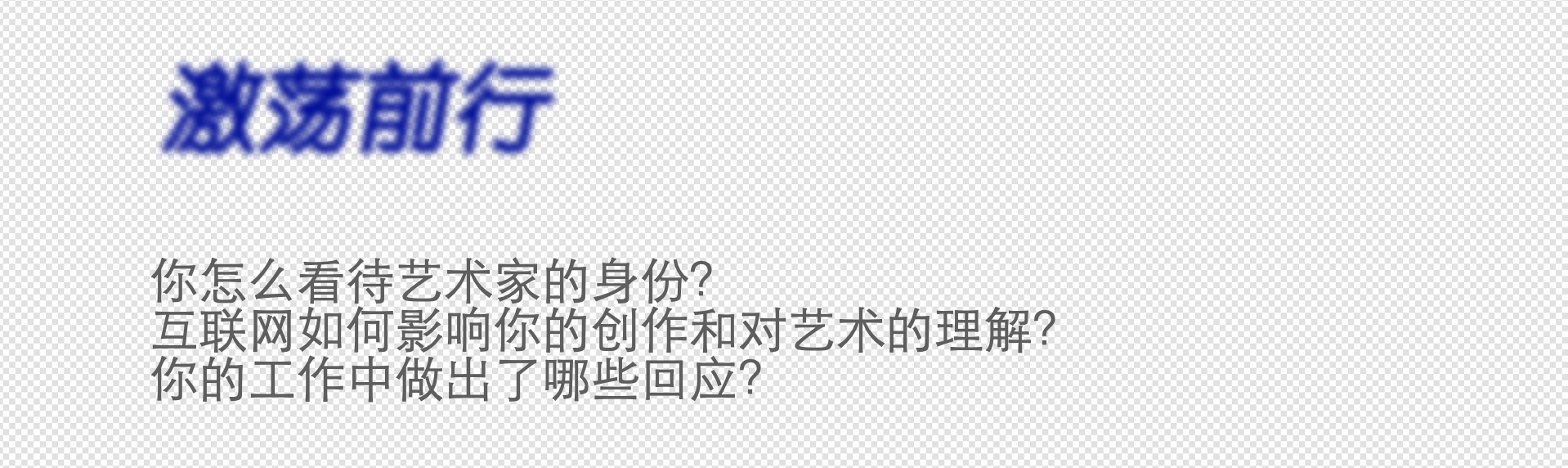
郭:我们这些艺术家都有纯艺,电影理论这类的背景,首先我想让大家谈谈对艺术家身份的看法,包括像陈霄也在做一些商业品牌的项目,你觉得艺术创作和你其他的工作间有什么关联?
陈:在我这边已越来越模糊,我没有办法去真正界定什么是艺术家的身份,感觉好像你只要是美院毕业,且你想一直从事艺术创作的话,你就可以是个艺术家。之前我和啟栋在法国聊过这个问题,我觉得当你觉得自己是艺术家的时候你就是一个艺术家。我认为还有很多工作会和艺术有关,都是把想法通过各样的形式表达出来,那也是一种艺术家的存在形式。我觉得不需要外界来界定一个这样的身份,也不需要这样的标准。在我现在看来这也没那么重要。
郭:那啟栋呢?作为策展人,你是怎样挑选艺术家的?你会怎么安排他们的作品和身份的关系?
孙:其实当提到“艺术家身份”这样的话题时,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评判的规则,而不是单纯地说我想做什么创作,“主动性”已被剥离了。其实陈霄提到“模糊”这个概念,刚好也是这次的议题,我看到咱们四个的头像也都模糊了起来。我很喜欢这个头像,模糊的处理可以把敏感度给降下来,将原来“艺术家”的鲜明特征给模糊起来。到最后你发现这个“家”可以是一个“家族”,是很多打着艺术家这个旗号过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但他们被你发现的时候也是充满野心的。从艺术人到艺术家会经历一个过程,艺术家这个身份只是一个最终的结果。
周:作为艺术家,我对媒介,语言都很感兴趣,且将数据与算法融入创作中。我认为媒介即是信息本身,通过新媒体进行艺术创作这一行为本身已突破了传统界限,新媒体艺术依赖于互联网传播中的复刻过程,这也已然脱离了传统艺术市场和其中的销售模式。以往的物件交换和转移也因此被信息化。艺术家身份的模糊性是内化其中的,可以利用这个身份做很多元的事情。作为艺术家,对这个时代有话想说,那种想表达的欲望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艺术性”本身。
话题2. 商业项目和艺术的边界 & 商业跨界是如何支撑个体创作的?
一种悖论与自我博弈 :具有目的性的艺术处理 & 艺术家本人的表达诉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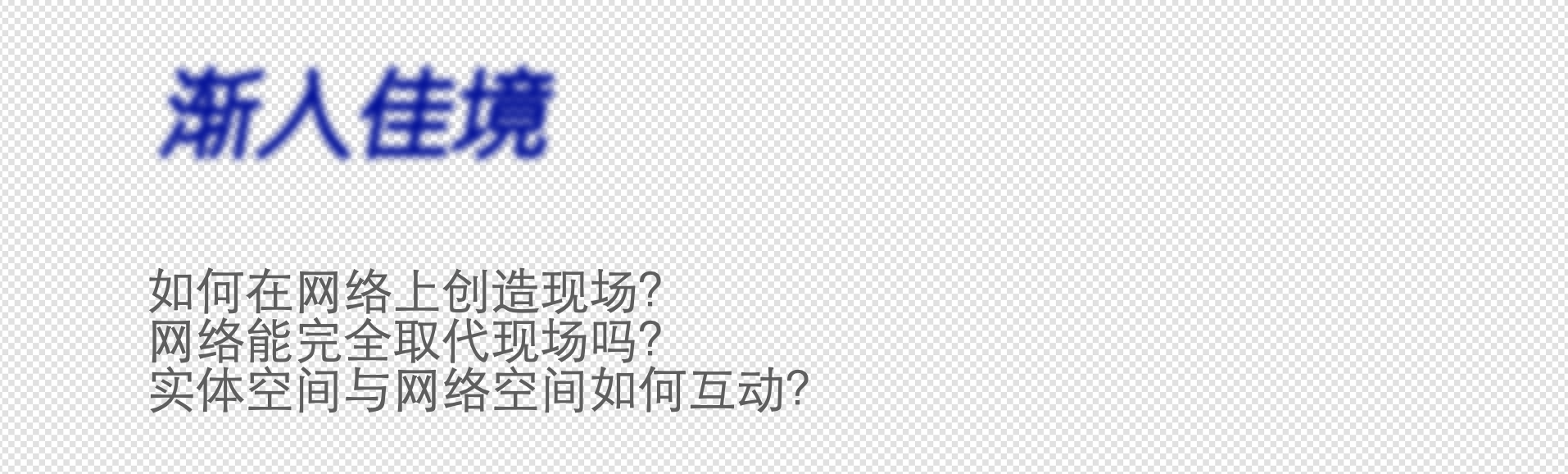
郭:那么这种新模式可以怎么和市场融合?艺术家以何为生呢?
周:我自己会开发并参与一些项目,如驻地项目,基金会等等。这可以用来支持自己的艺术创作,从而不受市场的左右。我非常看重自由性,追随兴趣去继续挖掘,也是艺术家生活的一种本质吧。
郭:我们选择去做一个商业和跨界,是为了让自己的创作条件更好。但艺术家的大规模跨界会是一种对策展人的身份的挑战吗?
孙:我觉得对策展人完全不是一种挑战,因为策展人的工作也是一种跨界。真正挑战的是一种权威,一种机制,那个机制是属于整个艺术市场的,一套传统的逻辑。
郭:我在采访过程中也会涉及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很多人会探讨设计和纯艺的边界。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Design for you, art for me”。带着一个目的去做的一种跨界的艺术处理就是设计,他是对艺术家的表达诉求做了一个更形式化的体现。设计产品是在提出问题的同时给出解决方案,而纯艺没有这么多框架,可以异想天开。
陈:我正好可以聊一下这个话题,我之前在法国参与过有关艺术和设计间的关系的讨论。设计更多是在回答问题,用于满足需求;而艺术会提出问题,包括一些艺术理论家,他们发起带有批判性质的思考,就会有更多的可能性。不过在中国有可能这方面的东西是缺失的。
比如我们去画廊看一些艺术品,我们会思考它们是为藏家而生的吗?比如现在有些画廊开在商业中心里,那它们是为商业而生吗?我们会发起更多的提问,比如为什么一个商业中心的展是网红的?就如之前所说,很多职业身份在变化是因为大量的东西是不明确的,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但反而那个也可以是更好的状态。
话题3. 互联网情境下的现代生活 & 艺术创作:“灵光的消失”(The Aura is Los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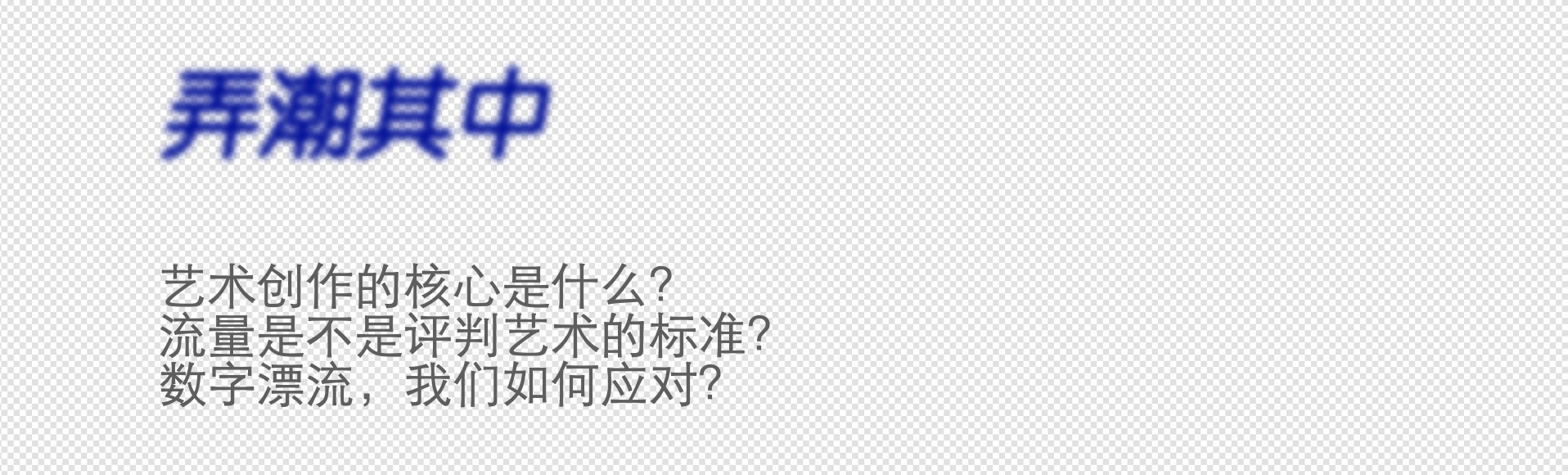
郭:这正好回到了我们要探讨的互联网话题,这也是我们在切身经历的一个确切的问题。 你们如何看待互联网对艺术创作的影响?不管是网络直播也好,还是别的新型网络形式也好,你们对此有新的发现或感受吗?
周:对我个人来说我真的是生活在互联网上,我每天使用手机的长度至少超过五个小时,我之前看过一个调查说中国有将近一半的人使用手机时长超过五个小时。我觉得这和以前我们看到的传统艺术也非常不一样,我们以前看的是山水,静物,肖像啊那些人们生活的状态,而那时他们的创作方式也是在自己的工作室里。而如今的生活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互联网上,比如我和我的父母到了海边,他们会想小时候和大自然间的关系,但对于年轻人来说,会想到在网上看到过这个场景。被我们称之为“打卡”的过程即为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这样的坐标,我们的线下就变成了这样的坐标的图示,成为了“网红打卡”。现在的网络就变成了我们的生活状态,我自己会很享受在网络上遇到的这种体验,也会去回应这样的体验。
郭:那啟栋,在你的策展经验中网络是重要的吗?
孙: 那首先我和姜杉不一样的是我不是一个特别合格的互联网使用者,我不会在网上投入很多时间,但我仍觉得这是一个正面,不需要否定的东西。我们在这里讨论“漂流”,但其实这个概念于我为言还不是那么准确,这也许指的是在互联网的水面上沉浮,但我个人认为更应该像鱼一样在互联网中潜浮穿梭,所以互联网于我的关系就更像水和鱼的关系,这带来一个启示是,生活和我之间的关系是有一种流动性的,需要一个主体,一个客体,而在互联网上的“沉思”应该被分来看对待,我们以前看待世界的那种静止的方式被互联网彻底颠覆了。
陈:我是因为现在在做一些商业的项目,其实我对互联网比较反感,因为避免不了所有的项目需要二次传播。不管是商场综合体也好,文化项目也好,都会需要打卡,可能是一个装置作品,艺术家在做跨界也是因为有这种需求,他们希望能有一个被“打卡”的点。比如老阿姨可能飘一下丝巾摆个姿势,年轻人也许穿个汉服拍个照片,有时候这些强度会大于我们的项目自己做的媒体宣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点。在我看来这里面是个悖论,线下的永远是在的,可触摸的。
郭:那可以谈一下你在工作中是怎么回应这种做法的?
陈:我更多的工作是做内容,所以对我来说我还是希望人能到线下,能来这个空间,这样人与人之间可能可以更近,和我们做的内容也可以更近。我无法想象如果你不站在这个画前你会感受到它的信息。因为在现场有我们的策展人,艺术家,这些理论的实践者构建出这个线下的艺术空间时是为了更好表现艺术家的作品,但是你却通过网络让观看形成了一种阻碍,它当然可以形成另外一种讨论,也会启发另外一种思考。但就对这个展览本身来说,我觉得影响还是挺大。
郭:正好陈霄的这段介绍也把我们的主题引到下一段,当互联网不断渗透到现实世界,现场,比如今天我们也有网络的直播,那请啟栋谈一谈美术馆在网络的推广下有哪些变化或影响。
孙:其实美术馆在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事物,但我们也有自己传统的艺术观看场域,比如佛教的洞窟,但区别是这些不是挂起来给人看的。人们吃饱喝足后会举一个灯把长卷打开来看,那是艺术欣赏的传统。建国以后艺术大师们的作品在我们的日常用品上被观看,暖瓶,脸盆,瓷杯子,那上面的图案可以是齐白石的画作,而那种图像会借此传到所有人的意识里去。之后大家开始有机会进美术馆里看原作,当代艺术一直创作到直至零几年,人们才开始意识到美术馆在干哪些事。你看现在上海广场有个没顶的展览,二十一年前,九九年时那里想自己凑钱办一个展览,结果开了半天就被警察查封。而现在反而是商场要升级装修了请他们来办一个展览,这是一个全社会开始迎接的这样一个新状态,这也反映了我们对“现场”的新理解。
而同样的技术在网络上,比如VR技术等,我们会把展览以VR的形式给人观看,哪怕展览结束了也可以点进一个链接,在里面环游。我不保证这个环游的姿态会让你真正了解和感受这个作品,但它可以作为一个文献,一个archive(存档),供有兴趣的人在以后激活,唤醒。所以我觉得现场和网络还是两条线,互相间不可替代,但同时它们也不能没有, 像我们在上海,在江浙沪的可以来看这样一个展览,可以来体验,但如果说你在国外呢?特别是疫情之下。在新疆,西藏呢?你无法来也来不了,这时候VR也许就可以满足这个需求。
我在一五年的时候在敦煌看了三天莫高窟, 但敦煌的人告诉我如果我再晚五年到十年,一般人的话只能给他看数据的这种,只有可能是有特殊研究需求的人,才可以看到真正的这个东西。后来我想找个地方喝咖啡,就进了一个咖啡厅,整个商业特别萧条,但咖啡厅里面打扫得特别干净,虽然装潢是落后北上广的,特像我们小时候体验的那种“雕刻时光”类型的咖啡。里面有三个年轻人在打理自己的空间,他们把咖啡给我上来后他们就自己在聊天,做自己的事情。我从那个氛围隐约地感到他们其实就是,比如说在外上学的人回到自己家乡,渴望在敦煌有跟北上广,跟纽约巴黎一样的城市生活。他并不想看莫高窟,就想守在这个咖啡厅里体验北上广的人在想什么,在刷什么样的剧,在买什么样的衣服。你可以看到网络对他们来说有多大的吸引力,可以这样满足一个想象,所以我觉得从公平的角度来说,网络又非常的友善。
郭:太精彩了,现在可以交给周姜杉谈一谈数据艺术的概念在网上如何呈现?
周:我觉得我可以对陈霄的“现场”提供一个补充,因为我真的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面。我讲一个自己的经验,就是之前在荷兰的时候去梵高博物馆看梵高的作品,前面围了好几圈的人,我离那个作品其实非常的远,然后又非常热,因为人太多了,我什么也看不见,更别说理解什么。这个时候我就扫了一下码,我就开始看这个作品的介绍,虽然这个介绍我可能平时也会在家里看,但是在现场的时候我看着介绍,有这个导览,然后我看到还有其他人也在看,我发现这个时候我跟梵高的画的关系比我远远的看挂在那里的画还要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以一种另外的“现场”和作品发生关系。
说到最后,其实是我们如何能跟创作或者说跟内容本身发生关系,不管它是线下还是线上,像啟栋刚才也说到了“现场”,我们怎么去区分线下的是现场,还是线上的是现场?比如说像我们做一个社群项目,或者说做一个公共项目,公共性社群性肯定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如果我在线下做的只有5个人,你们说他叫公共项目吗?但是我在网上发起一个什么讨论,结果有100万人参与,他就已经具备了公共性,而且他有现场性,还有时间性。
但是网络的特点和线下其实它有非常多不同,比如像刚才我们也聊到网络信息的快速流动化,因为过去的我们在对于一个传统的这种实体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它一直在,它是一个安全的存在;但比如像我们今天发的朋友圈,我们的点赞明天就过去了,所以这个坐标它时时都在变化。我的每一次的感官伴随我刷抖音的这么一下就进行了跳转,通过刷抖音的过程我不停重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非常不同的地方。
所以,这样两个东西(线上vs.线下)怎么去结合它,怎么去看待它?首先我觉得只要是我有身体的一天,那这种实物性的东西就必须存在,因为我和它有身体的接触;但在另外一方面,我们有大量的时间在互联网上,不可否认当我要去哪个地方体验一个实物的东西真的非常远,我两年才能去一次海边,但我知道网上的经验是每天都在,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离我特别的亲近。
陈霄:我还好奇一点,其实我们一直在讨论网络所重新界定的“人”,“货”,“场”三个概念,对不对?这个里边就会牵扯到那“人”,我们都明白对吧;“场”,我们也明白;我们是不是用互联网重新去界定,比如说整个艺术的系统的话,艺术品本身它是不是就成为了“货”呢?
孙:不光是艺术品是“货”,人也成了“货”啊。
陈:我觉得我们一直没有离开这三个词,包括为什么我们国家会特别重视互联网,大家都在讨论,尤其是姜杉有一次跟我说,他从英国刚回北京的时候,就满大街连快递小哥都在说我要超越,做什么互联网做电商之类的。其实特别可怕,但其实它就是因为重新界定了“货”的概念以后,它给到了很多人以生存的机会,否则的话如果可能在传统的这样的一个“现场”里面,或者是我们的物理空间里面,他给出的这样的机会就很少。因为它是所有的东西都讲究仪式感,门槛,就我要进入到这个厂里面我一定是要跨越门槛,够得着才能进,然后才能去接触到货物。
郭:陈霄在描述自己的项目的时候,他觉得实体空间是不能取代的,现场的“场”它重要的是什么?刚才我们说到是不是有传统的这种灵光(Aura)的闪现在现场,你觉得现场还有哪些是网络上不能取代的?
陈:很好,这个还真有一个挺好玩的案例。之前我和一个新媒体的艺术小组合作一个项目,然后前期我们在做讨论,然后网上找了很多reference,我们找到一个视频,应该是俄罗斯的一个新媒体的商业小组做了一段是两个芭蕾舞演员在一个很空旷的舞台上跳芭蕾舞,然后激光打到他们的身上在空气当中成一段段的段落。我们当时就懵了,一直搞不明白是什么技术这么牛的。直到我们拿了一台激光机做测试的时候才发现原来他在现场是做不到这样的感觉的。可能是把拍摄的摄像机的光圈调小一点,速度调慢一点,然后它就能出来这样的效果。所以说我就觉得工作当中,时常有这样一个比较难去解决的问题,我分不清楚现场应该怎么去把控。如果把它只归咎为一个视觉的体验的话,其实它很多东西是非常单一的,它是缺失的,我还是相信人身上他所有的感知应该是并行的,你才能更好地去体验你想体验的东西。如果把它单一化的话,好像真的少了很多东西,或者你是不是真的在视觉上被欺骗。我记得我第一次体验VR的时候,我听到特别有意思的一句话说,其实它是在欺骗你的大脑,这是在我的工作当中会去反复去想的这些问题。
郭:好,下面我想请啟栋聊一聊实体空间与网络空间的互动,刚才姜杉提到他在博物馆在刷二维码或者一些信息的提示,那作为艺术场馆的运营,或者是我们谈到的博物馆领域,还有哪些网络的这种形式?
孙: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是,我们在传递什么内容,什么内容是要通过线上传递,什么内容需要通过网络去传递?其实我不是说会把网络或者现场当做是一种工具的问题,而是说,在我看来每一种所谓的一个存在物,一个客体,它都有自己的逻辑。因为中国人特别善于去讲究经适制是吧?一个东西我们把用法研究好了,我们好好用就可以了是吧? 其实这特别简化互联网思维,你比如说互联网公司的很多高层,像我这30多岁,人家都是财务自由,年薪几百万,但我这个,人问你这能赚钱吗?怎么赚钱呢?我就替你们想好了,不要去赚钱,因为这里有粉丝经济,我们一线,二线,一直到18线城市,它把所有的写起来就有人养着你们,就能活着。你看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他可以把这个一切都拆成数据,人也变成数据,如果有这个数据量了之后,我们就可以就完成变现的工作。比如开发一套游戏,那我们进来一天几十个亿,几百亿,都不要一天这事儿,大年初一那天晚上就好几十个亿,你看所以这对他们来说,我们没有一个内容,只有一个数据的交换,是吧?
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不是完成这个工作的时候,我给你就是一比一了,咱们就把钱挣了;我们传递的是货真价实的内容,附在这个平台之上的内容,所以说我们是做内容的人,我们就不要老觉得自己是做平台的人,这是完全两种思维。所以我觉得对于实体空间和网络空间的这样一个互动的问题,对于我们美术馆来说,我们是做内容的,只有这个东西就成为叙事,成为历史就会被流传下去,而不是说我用什么样的技术。
郭:好,姜杉,我们屏幕间今年推出了T恤和数码版画,这也是在长时间来我们在网络上运营积攒了数据之后,然后我们进行线下的一个互动和沟通,你可以介绍一下这方面吗?
周:我谈一下我对线下和网络的这种关系,因为我会把他们都理解成是不同的媒介。首先不同的媒介虽然都是内容,但它们承载内容的方式会完全不一样的。比如我要设计一本书,无论你怎么设计都是书,它的这种文字型的存在或图片存在,这个书它只能存在这个东西。当我们要把这个书的内容制作成一个影像的东西的时候,可能它的形式就会变成一个电影。当我们把这个内容存在在互联网上时,它会需要更多的网络这种媒介所要求的信息。
现在有很多的这种艺术项目,当谈到互联网的时候,可能第一个会想到是说把它3D拍下来,给变成一个VR的场景;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个在互联网上应该有的一个状态,因为那是在互联网上对线下的一个想象,但是它并不是一个互联网延伸的语言
当我们刚去看比如像早期的新的一个媒介出来,比如说iPad出来的时候,最流行的这种APP其实是电子杂志,当时各个品牌各种媒体它都有电子杂志,因为在那个时候大家对这个媒介还不熟悉,大家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老媒介的东西放上去,但到今天我们会发现 iPad的这种形式,APP的这种多媒体的关联性其实变成了完全另外一种方式,已经和我们之前所看到的那种杂志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线上和线下两个媒介非常不同的一点。如果我们要去做线上的话,我们首先就要考虑线上的媒介它能够存在的状态是什么。
我觉得比如今年上半年直播特别火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也看直播我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呈现了我们在线下的一种社交状态,比如说我去一个美术馆开幕,这个时候人挤人,有时候我可能台上的表演很无聊,我可能会跟旁边的人说一下话,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能跟认识到的人会聊天,这是一个我们去参加开幕,去一个线下展览或活动所拥有的体验。
直播其实和线下开幕的形完全不一样,它是一个非常平面的东西,但它也创造了基础相似的体验。比如说这有很多的人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有上面有人进来,还有人在聊天,然后我觉得他说的特别有趣,我可以点下他的头像,我看见他的profile,然后给他发个私信,这个过程虽然它跟线下非常不一样,但它却创造了那种线下活动的一种设计感,所以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当我们要去做线上项目的时候,它的形式首先跟线下是完全不一样,但却创造了人们在线下去获得的这种社交体验。
对于屏幕间来说,大家会发现这些作品其实都是非常平面的,也跟我自己对于这种线上的语言认知有关系。大家早期看互联网刚出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像second life,每个人在里面有一个相对的形象,每个人都在虚拟世界有一个直接的空间,但当 iOS7出来的时候,突然提出了扁平化,开始抛弃现有的参考,这像我刚才举iPad的例子一样,互联网开始有它自己的语言,因为互联网的特性就是要快,要快速达成这种信息的传递。当我跟啟栋想说一句话的时候,我们两个还要约个线下找个咖啡,我觉得在线下做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慢而且很麻烦的事情,我就只想发个微信一句话,告诉他这是什么事儿,这是线上媒介所拥有的特点。
今天大家使用社交媒介,我觉得这个已经是最鲜活的这种表达,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去承认大家今天使用平面媒介创造的内容,我觉得屏幕间其实想说的是这件事情。刚才提到说我们屏幕间开始有T恤,有装裱,和数码输出,其实在一开始我其实想这个问题想了很久,有很多人说跟我说做屏幕间你就应该是纯虚拟的,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点,我认为一个新媒体的东西,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信息不会局限在一个特殊的媒介上,它应该是可以被无限复制的。
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像现在这个行为表演艺术家表演签字这样,他的表演不留下任何的记录,他也不留下合同,所以他就去物质化,不希望自己的东西出现在任何的,物件的东西记录的上面。我觉得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当你这个信息出现在所有的物件上的时候,那这个物件就没有办法再去定义它。
郭:好,我们进入最后一个话题,那艺术创作的核心是什么?刚才大家都谈论了,每一个创作者可能对于这个问题的观点不太一样,然后流量是不是评判艺术的标准?我觉得也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今天我们刚才说到数据,说到实时,说到互动,今天我们的互联网,我们的直播,这些线上的内容已经可以数据可视化,透明的,然后艺术可不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流量是不是可以通过数据来判断它的好坏?
孙:说到这我又突然想到了,是Tik Tok刚开始被美国政府要攻击的那个时候,当时有一个美国的华裔的科技这种的博主写了一篇文章专门分析了这个事情。那篇文章里面有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文化有时候是可以被抽象定义的。
比如以前说我们做一个科技公司,比如说IBM来中国拓展市场,我先看一看中国人喜欢什么,中国人的民族性是什么,中国人忌讳的什么事我都摸清楚了,中国人的红色文化一个什么样的等,然后我们组设计团队。但现在这个不是这样子做的,比如说Tik Tok,他们推广最好的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印度。印度有各种方言,可能有几千种方言,你不可能是说你派出这个工程师,他还能听懂各种方言去筛选人们喜欢看什么,不看什么;这都没有,他靠的就是他的算法。你可以看到屏幕的那一边是不同的印度人在刷不同的短视频,但这一边全是中国工程师。所以当时那个博主,因为他之前在国内的上司是一个很高的工程师层的管理人员,他就问说这帮人懂英语吗?没有一个人懂,但靠的就是算法不断给他们推广。
所以通过这几个案例,文化是可以被抽象的,我们反过来问流量是不是品牌的标准,当然是,但是不是唯一的?当然不是。
就好像我们对于公众话题,如果有一个人讨论了,肯定是没有公用性的,但1亿人讨论完后马上就散掉了,这个话题最后你应该怎么去给传递下去?流量是有了但两个小时后新的事情就出来把原来的掩盖掉了。所以我认为对艺术品牌也是,如果有很多人来关注,这是一个好事,证明大家有兴趣来关注这个东西,但如果我们反过来,我们只认为这个是最重要的,我们去为了流量而流量,最后就变成了大众消费的一个层级,因为对大众消费来说,我们是需要消费艺术,他们消费很多东西,你自己主动降低到这个层面之后,你就是消解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周:我觉得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首先你必须是真诚,而且你做的每个项目可能有不同的你要去表达或去实现的目标。像我刚才提到的,如果你做的是一个社群项目,有多少人参与,有多少的公共性,它显然是它的一个标准;但如果你做的是一个关于你个人的项目,其实有没有人观看是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件事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非常的享受,遇到困难的时候去找出问题的答案,然后跟别人交流,在这个过程得到了启发,是一个非常愉悦的过程,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不需要用流量来证明,对,但我觉得在做公共项目的时候,流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郭:我想几位嘉宾在这个话题下面回答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数字漂流我们应该如何应对?一个简短的句子来结束这回的谈话。
陈:我觉得之前是一个很大的标题叫数字漂流,作为我个人来说,我是有一定的无力感。因为就像葛饰北斋的那张画《神奈川冲浪里》,它是一个巨浪,当它过来的时候,你的那艘船才这么小,你这个时候只能让你的这艘小船不翻,然后坚守你自己想坚守的东西。浪再大也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但是可以做一些改变。其实它不是一个漂流的问题,它是一个数字的洪流,更危险,它会有漩涡,还会有湍流等等的情况发生。如果以艺术家的身份来说的话,我觉得应该用艺术家自己应有的智慧去去应对它,或者去解决这样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当然也同时去掌握它,可以让它成为你的工具,然后更好的创作和表达。
孙:那我觉得其实把自己变成鱼,在这个数字的海洋里,可以如鱼得水地穿行,这样好好生活下去。
周:我觉得就是要真诚,秉着你自己对一件事情的理解,而不是说可能看到这个风浪过来就不去追寻。因为我做了这种关于科技还有编程方向的这种创作,那有人就说如果有一天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去创作作品的话,我们还需要什么?比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人工智能有谱曲,绘画,我们是否还再需要去创作的东西?首先创作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体验,而且在我们去观看一些图像的时候,和在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可以获得了这种创造力。所以它并不是物件本身,而是要回到人自己如何对事情产生理解,不是看这种表面的呈现。
郭:做一个总结,我想在面对这个数字的情境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没有冲突,但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从某种角度上有不同的目的,有商业项目,有美术馆的展览,也有我们在网络上的艺术项目,我们看到了非常多元的一个网络生态。对于我,也是从一个媒体的身份,我采访了很多艺术家,很多新的样式,新的形式,我想对于我自己来说还是弄潮其中,就是像葛饰北斋一样,我们那个船要翻到浪尖上,要有这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想今天来的都是年轻人,我想大家如果能够投身到这个浪潮当中肯定会有新的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