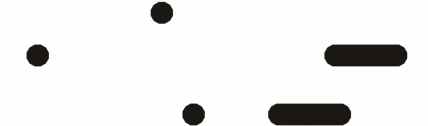艺术家:阿娜利亚·萨班、奥斯卡·穆里略、达米安·奥尔特加
时间:2017年11月10日 下午2时
地点:油罐艺术中心工地 龙腾大道2350号
举办者:上海油罐艺术中心、《艺术界 LEAP》
2017的11月,正逢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期间,阿娜利亚·萨班(Analia Saban)于乔空间(QIAO SPACE)的个展“颜料上的画布”开幕,上海油罐艺术中心(TANK SHANGHAI)与《艺术界 LEAP》共同举办了一场精彩的论坛:“无中生有:艺术家想象未来美术馆”,由《艺术界》主编岳鸿飞(Robin Peckham)主持,邀请三位杰出艺术家——阿娜利亚·萨班、奥斯卡·穆里略(Oscar Murillo)、达米安·奥尔特加(Damián Ortega)展开了一场关于理想艺术机构的深入讨论。
与主题”无中生有“十分契合的是,论坛正是以油罐艺术中心建筑工地为背景的——4位嘉宾就在TANK SHANGHAI的诞生地,就艺术家眼中的理想美术馆进行了 “此时此地此景”的思想碰撞,表达了各自的思索与期许。
艺术机构应当如何平衡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国际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美术馆是否具有精英主义倾向?如何平衡艺术与娱乐?艺术多大程度依赖于语境化?艺术机构如何在艺术生态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与由此生发出的探讨无疑为筹备中的TANK,以及许多新兴艺术机构提供了多重思考维度。
【精选片段】
Part1:艺术机构从无到有
Robin:今天的话题“无中生有:艺术家想象未来美术馆”,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理论的问题,而是近来变得愈发重要和紧迫的现实问题。上海涌现出许多崭新的美术馆,如此讲既是因为它们完全是无中生有、拔地而起的,使得我们把大片的土地,美丽的历史建筑,在短短几年内变成了文化机构;也是由于它们并没有包含什么知识文化遗产,来理解美术馆究竟是什么,这个现象很危险,令人不安但也令人兴奋。因为这意味着艺术家、年轻策展人将有机会从最初阶段开始,参与到这些机构和空间的建设中去。所以我很期待今天谈话中将能够听到,你们与其中一些机构合作工作的经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世界的。以及,你希望在未来这些艺术机构会做什么?
Analia:我在纽约的时候,总是很难想象,这些美术馆是怎么开始的?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Solomon R. Guggenheim Museum)、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惠特尼美术馆(Whitney Museum of American Art)是如何开始的?像这些非常专业的机构,需要几代人来建构。今天在纽约逡巡的时候,光是想象开端就很难了。然后突然间,我在上海呆了三天,我在见证这些大型机构是如何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形成的。作为一个艺术家,这令我印象深刻。看到如此重要的事情的萌芽阶段是非常鼓舞人心的。这次上海之行,我很荣幸能和乔空间团队一起工作,看看是怎样的愿景创造出了这样的机构。我感到兴奋,而这种兴奋是极具感染力的。我带着憧憬与希望回家,在这次旅程后,我的心中仿佛点亮了一束升腾的火花。
Damián:对于这个问题我在想,我们期待从博物馆得到什么?我们又在等待什么呢? 当然,建立一个崭新的空间对每个人来说都像是一种幻想,同时也是在展开一项新的事业,获得新的体验。因为这总是我们的希望、梦想和期许--去探索我们未来想要什么,未来艺术会怎样。我想到我的女儿们,也许她们将来会成为艺术家,但再过一些年,艺术一定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 The institutions have always been private. MoMA is the biggest private mafia, in terms of institutions."
——Oscar Murillo
Oscar:显然欧洲现在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文化危机,欧洲的机构没有资金,所以这在某种意义上拓宽了“竞技场”。我认为并不存在一种给定的方式。我的贡献是思考拉丁美洲之内新的联系和关系,我认为这很有趣。对于中国的机构、藏家或私人机构来说在美国和欧洲之间往返太容易了,而非洲和拉丁美洲才更具挑战性。(艺术)机构一直都带着私有制的烙印,在机构层面上,MoMA(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可以说是最大的私人帮派。万事总有一个开端,我想也许中国现在正处于这个开端。现在说太多实在还为时过早。
Part 2:艺术家如何想象未来美术馆
与艺术博物馆合作的早期经历
Robin:但首先我想听听你关于博物馆的个人经历,在你职业生涯的早期,博物馆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如何与策展人、机构收藏、教育部门一起合作?
Analia:我在洛杉矶工作,那里有很棒的机构,非常好的博物馆,尤其是哈默美术馆(Hammer Museum),它是那种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你很快就能沉浸其中的美术馆。还有洛杉矶现代艺术博物馆(MOCA)和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LACMA)。LACMA意味着一种更宏大的对话,作为洛杉矶郡立的博物馆,它以更广泛的方式收集展品。
我非常感谢与我合作过的策展人,是他们成就了今天的我。刚出大学的时候,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艺术家准备起步。首先他可能会结识某个机构的年轻策展人,一开始只有这一个人,他每六个月会来做一次工作室访问,激励你不断努力和成长,可能短时间看不到什么成果,但这些策展人仍然与你一同前行,从一个变成两个,从两个变成三个,我和那些早期的老朋友们已经合作有十二年了,并且仍将继续。我非常感谢他们,以及他们将我的工作与国际背景联系起来的方式。
另外我也想对画廊和商业系统表示感谢,通过这个系统我和画廊愉快地合作,一起努力工作去接近那些机构,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竭尽所能进入那些机构。还记得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作品在洛杉矶郡立艺术博物馆(LACMA)展出时,我意识到自己从事艺术的意义就是这个。我之前的作品都在画廊展出,这当然也很好,但只有与艺术相关的人才会来看。突然之间,我的作品在博物馆中展出,被精心地置于某个语境之下,向包括孩子的普通观众开放。这完全改变了我的艺术实践。这就是我与美术馆的早期关系,它如今也驱动着我的日常实践。
公告性立场
Robin:谈到私人意义上的收藏和成为博物馆的收藏之间的区别,后者是一个旨在成为面向公众、教育和历史的东西,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一个较小的收藏空间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又或者你认为私人收藏应该建立在一个更具机构性的公共立场上么?
即使是商业画廊也办过很好的展,就像那些优秀的机构展览一样,所以这变得很难区别。当然那些伟大古老的博物馆将永远是伟大的传统博物馆,无论从收藏还是从历史上看,都是如此。阿娜利亚所说的哈默博物馆(Hammer Museum),它是一种较小型的机构,类似于伦敦的陈列室(Showroom),还有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等等。这些较小规模的机构对于年轻艺术家来说非常重要。我并不是在暗示私人收藏应该与年轻艺术家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但我认为这是一种“交叉感染”(cross contamination),具有积极的影响,文化得到支持,机构也会越来越多。
“Culturehas become a currency also beyond a kind of commodity, and the biggest cultural commodity is western cultural commodity.”
——Oscar Murillo
但文化也超越了任意一种商品成为了一种货币,最大的文化商品就是西方文化商品。非洲这么大一个大陆,却并不怎么为人所知。然而,在某种程度上,非洲甚至是现代主义的发源地。或者说在西方的阴影中不断前进,那里存在着各种各样未知的探索空间。但我只是在思考未来。
“I'm betting on these new initiatives to potentially be the respectable or to become the respectable institutions of the future.I believe that as an artist, I ought to question everything."
——Oscar Murillo
Analia:如果收藏与学术对话完全隔绝的话,那它就会经受痛苦和带来隔离。一方面,你(艺术家)需要这些有远见的人,他们让事情发生;另一方面,因为处于隔绝状态,收藏会迷失。因此,收藏的内容也很重要,与更具有历史意义的学术机构进行接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很难去平衡。我在一些城市看到有真正的大收藏家,比如达拉斯(Dallas),所有的收藏家都真正是博物馆的一部分,他们都把作品捐赠给博物馆,他们是真的在与博物馆合作,而在其他一些城市,藏家的收藏品是孤立的。我认为这样对话变得有些无力,而且很受影响。
Oscar:哪些城市呢?(阿娜利亚:比如......迈阿密。)但迈阿密有不少美术馆,有私人机构、基金会的生长及扩张,也许它是逐步的。如我之前所说,MoMA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博物馆,并且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机构,当然因为,它已经完善到能够雇佣具有博士学位的专业策展研究员。但它当然也有很多垢弊。然后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出现了,至少是一个新的机构,但是当然,这是伦敦历史轨迹的一部分。所以我把赌注押在这些新兴机构上,它们很有潜能,可能会在未来成为非常不错的机构。
我们是当代艺术家,我想我也对历史持怀疑态度,历史无法是完全客观的。所以我不会说,因为书里这样写,所以历史就是这样,例如《圣经》。我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应该质疑一切,就像科学家一样。一个人必须质疑,而不是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
我现在快速读一段话,“约翰·保罗·盖蒂(John Paul Getty)是一位美国实业家,他创办了盖蒂石油公司,1957年,《财富》杂志将他评为最富有的美国人,1966年,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给他取名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公民,他的总资产约为120亿美元,按照2016年的标准,这个数字不到70亿美元,远没有90亿美元。”这就是我想说的,盖蒂现在显然在拉丁美洲、洛杉矶等地是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形象。也许现在我们可以期待看到相似的故事,只不过是在亚洲背景下,尤其是中国。我没有特指任何人,但现有可能是二三十年后故事的开端。我对回顾和把文化体系浪漫化不感兴趣。我们是有一种全球性特质和能力的幸运儿,也许我们应该放手去做,把赌注押在尚未发生的事情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很多人虽跟这个国家(中国)毫无关系,却仍然来到这里。我们在与亚洲人、中国收藏家、策展人、教育家建立一种关系。我觉得也是时候和非洲大陆建立起这样一种更深入和紧密的关系了。
机构风格
Robin:你认为什么样的展览或机构可以被称得上是值得尊敬的呢?这里“值得尊敬”并不是指富丽堂皇的宫殿,而是作为一个艺术家,什么东西能严肃到促使你想认真打量它? 你的标准是什么?
Oscar:我的心态很开放,一直都在与机构进行接触合作。我最近去了慕尼黑的艺术之家(House der Kunst),历史上它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机构,但现在是2017年了。三年前我第一次遇到策展人奥奎•恩威佐(Okwui Enwezor),他是慕尼黑艺术之家美术馆的主管。自那以后,我们一起分享、讨论、做工作室访问,后来我还在艺术之家美术馆做了个展。对我来说,这里的机构指的就是他个人,他在进行一场讨论当代生活的两难困境的对话,这个问题是被限制于某个时代语境之下的。机构总是在变化,总是充满了某个时代的作品,我们不应该将自己也限制其中。我对年轻策展人很有信心,他们以后会成为我们的“同代人”,这就是我对机构的定义。
Damián:我不完全同意你的说法,你说机构就像是一个人,它有名字、家庭、个人喜好。我只是很享受一种感觉--但你看到美术馆中的一个展览时,你不需要知道具体作品、系列、来访者是哪些,但你可以参考奥奎·恩威佐或者是引起你好奇心的主管或策展人的喜好,就会对这个机构就会有许多了解。因为你在之后的几个月一直会与之对话、在之后的几年观看这些项目。但另一方面,我真的很尊重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的人员结构设置,策展人们来自世界不同的地区,分工不同,结构多元。我欣赏这一点,虽然这并不总是奏效,有官僚主义和其他种种问题。事实上,我更喜欢那些有品味的策展人,他们选择自己想要的并呈现出来,我认为个性应该先于机构。
艺术教育
“I think of what art means to me and why I'm so grateful to be part of this,is because it is a language beyond language.A communication that goes beyond language,a communication that goes at an unconscious, it deals with the unconscious."
——Analia Saban
Analia:我喜欢住在洛杉矶的原因之一就是盖蒂中心(Getty Center)有一个超级棒的艺术图书馆。它是一个研究机构,主要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档案,可以看到艺术家的日记,或者可以看到 哈罗德·史泽曼 (Harald Szeemann) 所存档的一切。那地方像一个仓库那么大,只为存档,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个研究图书馆是我在洛杉矶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当我去到纽约,想写一篇论文的时候,却发现纽约没有像盖蒂中心这样供人做研究的地方。作为一个学生,你有获得研究资料的特殊权限,而MoMA图书馆只在早上9点到下午5点开放,且书的数目有限,必须预约。而盖蒂中心的艺术研究中心几乎全天开放,可以查阅无数的资料。
如果能有一个上海的艺术博物馆成立一个很棒的研究图书馆,不仅收藏有西方艺术,而且能真正地去捕捉那些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非洲、中国、整个亚洲的所有事就太好了,因为来这里(中国)我就是想要来做研究的,我是一名艺术家,但在这里我希望是一名学生,所以我希望多看多研究,对于艺术机构我也有同样的期望。若在这里看到罗伊·利希滕斯坦 (美国波普艺术代表艺术家)的作品,我可能只会忽略它,因为我真的很想看到一些我以前没见过的东西。我想到了解世界各地的当代艺术。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悲哀的是,在西方世界,我接受的整个教育中只有一节关于亚洲当代艺术的课程,而且还没有拉丁美洲艺术史课程。即使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这么享有盛名的大学,大多数课程都是基于西方艺术的。最终你会意识到你是多么无知却目中无人,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旅行得越多,就越发现对这个世界知之甚少。所以我希望把重点放在教育上。
我想到艺术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以及我很感激能参与其中的原因——它是一种超越语言的语言,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我可以在上海与乔空间合作展示我的作品,虽然我们不会说同一种语言,我不会说中文,他(指:乔志兵)不会说英文,但我们仍然可以做很深入的沟通,我认为这对我来说是最基础最重要的,这让我确信自己每天做的事,这是鼓舞我继续下去的原因——艺术是一种超越语言的交流,一种潜意识的交流,我们试着去定义和描述它,但却最终找不到合适的词汇,这更像是让你的身体去感知艺术,这对我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我认为博物馆应该挑战标签,解决标签缺失的方法是通过教育,像更深入地了解概念。我确实喜欢那些具有很好的教育部门的博物馆,我喜欢那些每天都有孩子和学校参观的博物馆,因为那是未来,我与乔先生就油罐艺术中心项目进行交流时也谈到了这一点。我的小女儿就喜欢去那种大美术馆,她才21个月,我非常高兴这是她想要的,他们的兴趣与好奇心引起学习的欲望。因此,我真正关注的是超越语言的教育。
“So I think as public engagement, and a lot of emphasis on education and to remember that culture can also be entertaining for their mind in a deeper way and it's very important to nurture those desires of their intellect.
To cultivate yourself is very important."
——Analia Saban
Analia:我想简要地提一下娱乐的问题,以及为什么它成了美术馆的竞争对手。关于冰淇淋博物馆(Ice Cream Museum),我根本不敢相信,只是门票价就要38美元,还全都卖光了。而人们有时还抱怨要花5美元去MoMA或者MoCA之类的地方。(注:MoMA全票为25美元)你们中可能有人不知道冰淇淋博物馆,我从没去过,但基本上就是个你可以去拍拍自拍的地方,它没有意义。你可以透过空气中的水雾,拍点儿你自己的照片然后上传到Instagram上。这竟然变成了真正的博物馆,实在太过骇人。文化可以以一种更深远的方式取悦思想,培养人们智识的渴望是至关重要的。我想对于美术馆而言,这是我们必须仔细思考的事。有各种各样的“病毒”,而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并谨慎对待“美术馆病毒”的发展。
“ There are all these other viruses, museum viruses going on that we have to be very aware of and very careful with. “
——Analia Saban
Oscar:对,但是那就好像是在说自拍和冰淇淋有什么错一样。自拍和冰淇淋有什么错?只是人们不再去其他美术馆才有问题。在我看来,问题在于我们预设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文化只存在于博物馆、当代艺术博物馆或历史博物馆中。也许事实并非如此。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理直气壮地假定博物馆应该是一个人流密集的地方?博物馆从来就不是一个人流密集的地方。虽然在墨西哥是不同的,博物馆已经长远地植入了墨西哥人的思想,而这可能是由于墨西哥的社会主义历史。但在西方,90年代的伦敦,博物馆变得很受欢迎,因为它们变得自由,内容受到影响,所以他们也成为了娱乐,成为了一个娱乐场所我们是否能够在一个更高的道德层面上说,我们是文化精英,因此他们必须注意我们? 可能事实正相反,世界也许就是对做其他事情感兴趣。
“ I still think there is value in art, and I really do.I mean, it's true, it does sound like a fraud sometimes,but then sometimes it doesn't.At least it's worth giving it a chance“
——Analia Saban
Analia:我只是在说我内心的感受,虽然可能只是我自私的愿望。去冰淇淋博物馆门票要38美元,这是真实发生的。我的意思是不想让一个小孩子接触的只是冰淇淋博物馆。我仍然认为艺术是有价值的,我真的这么认为。我知道有时这听起来像个骗局,但有时却不是的,至少应该给它一个机会。我只是担心,我们抱怨要付5美元门票去真正的美术馆,所以孩子们甚至没有机会接触到艺术。但随后我们心安理得地付了40美元去了冰淇淋博物馆,这就是个问题。因此促进公众参与至少会给人一个机会去体验,然后可以决定是否值得一去。
“And that is what I am championing when I feel it becomes a little bit fascist when it's like, “no, this is the only way”.
——Oscar Murillo
Oscar:我是同意你的观点的。我小时候从没去过博物馆。但就像我之前说的,文化无处不在。文化的“交叉感染”(cross contamination)随处可见。我个人不同意机构被预设为大众主义的。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地方,矛盾是重要的,我们是矛盾的生物。让我们更包容一些吧。
Robin:我想大家都有一种恐惧,害怕这个冰淇淋博物馆也许真的比艺术更有趣。我认为有一部分人只是想在喷雾中打滚,然后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有必要与之竞争,同时具有一定的娱乐性、趣味性和社交性。
Analia:比如,人们来到一个博物馆,然后就有乒乓球桌了,我不得不说,我们确实很喜欢打乒乓球,但是至少你之后会去看展览,如果它能让你在博物馆里多待一个小时,那为什么不呢? 也许博物馆里也有很好的餐馆,你知道它很酷,也许你会去喝杯咖啡,然后就顺便去看乔空间了。
现场提问者:之前说到人们宁愿去画廊或者冰淇淋博物馆都不愿去美术馆,你认为是因为美术馆的精英主义吗?你年轻的时候喜欢音乐,所有人都能沉浸在音乐里,但你年轻的时候,如果对艺术一窍不通,就会觉得此路不通,等你再大一些,你还是不理解艺术,你就再也不会去美术馆了,这是所有人的问题。美术馆和画廊有些精英主义吗?而如果这就是症结,它们为什么不能向所有人敞开呢?
Oscar:我是一个艺术家,我去美术馆也去画廊。但我第一次去画廊是18岁在伦敦东区,我想那已经算比较晚了。我住在伦敦,这城市是个文化气息浓郁的地方。整个90年代后期,我都浸泡在这浓厚的艺术气氛中,却对此浑然不知。当然,这并不是否认艺术世界的精英主义性,事实上它就是个精英主义的领域,也必须是。美术馆一旦不得不迁就大众文化,就会有些变质,因为他们需要各种达标,以换取政府的金钱支持等等,不过这也取决于你所生活的社会。我认为,比如在德国经常要求学校带孩子们去美术馆。而在伦敦,因为政策原因,90年代后期才开始这么做。不如这么总结,有些东西在改变,如社交网络某种程度上就是那种已经走在前列的事物。Instagram和脸书这些东西互动性很强,而且还建造了某种程度上的社群,即便很难接受,但这就是事实。而且我觉得冰淇淋博物馆要变成流行词了,不过这也是我们应该思考的。为什么冰淇淋博物馆要更加受欢迎?即便你要花40美元的门票,我想这说明了一些问题,这就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同时,我也认为美术馆没必要迁就公众。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应该在幼年时就开始艺术教育的原因。在美国,艺术教育根本不在他们的教学系统当中,艺术教育被完全从大纲、从课程表里驱逐了,我想它也被整个西方世界驱逐了。除非你去私立学校才能接受艺术教育,这样我们又要回到精英主义的理念了。在公立学校里没有艺术教育,我想这就是问题。
Damián:谈论精英主义总是很困难。在墨西哥它是一个大问题。因为文学正在被精英化,很多人都不读文学,他们只读过几年小学,甚至只是刚开始读他们就放弃了,人们不读书,是因为他们不能读。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社会政治结构比艺术或者美术馆更应该为此负责。因为我认为在墨西哥,美术馆对所有人开放,就和你说的一样,政府的对美术馆的支持投资需要耗费很大的比重,许多艺术家都为了国家赞助捐赠作品给美术馆,而人们去美术馆就为了借个厕所,以精英主义谴责艺术或者艺术家也是很困难的,至少不简单,负担和责任都非常重大。
Analia:我记得有一次去一家欧洲的剧院。歌剧院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很精英主义了,你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去理解一部歌剧。但是这家歌剧院不断地将剧院内发生的一切放映、投射到外面的世界。我想这就是分享,无论你在里面还是在外面,都可以参与其中。不过我也认为这是个正在发展的问题,而真正的缘由在于地理位置。
Part 3: 艺术与语境
Damián:能够从策展人那里得到反馈非常难得,因为他们都忙于在不同展览之间奔走,很少有时间交流。我在莫斯科的车库当代艺术中心做委托创作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棒的村上隆(Murakami Takashi)的展览,虽然对这位艺术家本人的作品我并不太感兴趣,但策展人为作品创造了“语境”,补充了很多内容和信息,如漫画、图片、文化历史和神话学的想象等,使艺术品反映出了更多的意义,比如政治隐喻。人们因此可以用更开放、崭新的视角去理解作品,这是我从策展人那里梦寐以求的。在这个全球化时代里,很多东西是碎片化的,尤其是艺术展览,你只抓住一个碎片,但是你完全无法定位或理解它,一切都很抽象。因此,我认为这样的语境,这样的背景补充,对拯救这种碎片化有超乎寻常的意义。
Robin:当在上海这样的地方做展览的时候,你认为需要多少文化语境,在多大程度上展示你的实践和作品?你想在多大程度上将你与教育、历史、地域和语言环境结合在一起?你会觉得你在表达更深刻更宏大的主题吗?
“Basically the work can be, can either be very very meaningful, or it can mean nothing. And it's really all about context."
——Analia Saban
Analia:对我而言,语境就是一切。语境决定了作品是否深刻和具有教育意义,使我们融入超越美术馆之外的世界,我认为我之所以在这里如此感到兴奋就是因为语境,因为这使我感到自己是比这个机构更大的东西的一部分,我正在与中国进行对话,而非孤立。
Analia:我想提一个我非常喜欢并正在研究的一个展览——“太平洋标准时间”( The Pacific Standard Time)。现在正在洛杉矶展出,它是由盖蒂博物馆(the Getty Museum)赞助的。因为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很多人都被流放过一段时间,使得一切都有些迷失和混乱,也没有档案。而盖蒂美术馆像是一个教育机构,它把资金分散到洛杉矶几乎每一个美术馆,然后基于拉丁美洲,办了八十个不同的展览,让策展人自己提出主题。我一开始还很担心,因为我会很疑惑,大家要怎么定义拉丁美洲?我怕大家会提出一些空泛的概念,但后来我发现这些展览实际上非常有用,他们专注于非常具体的主题和很细致的题目,比如巴西、阿根廷,或者某个特定的艺术家,从很小的切口不断深入下去,也没有试图去概括拉丁美洲的定义,或者说,他们并不满足于定义拉丁美洲。看了这些展览以后,我的确学到了知识,也能够理解当时的语境,并产生了兴趣。
Damián:我觉得做这样的展览很有趣,因为它就像是拉丁美洲或其他不同地区的一种延伸,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整合的。有些关于某个特定题目的创作邀请,总是让我很忧虑,比如墨西哥艺术、女性艺术或者非裔美国人艺术。因为最后,总会回到一个老问题: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他们到底有什么共同点?我对此真的很忧虑。现在对拉丁美洲人的描述是很开放宽泛的,我觉得这挺疯狂,你不能说我们的一些观点可以代表墨西哥的一代人,我们真的要努力去避免这种民族主义,或者任何将我们分成拉丁美洲人或者墨西哥人的标准,我们的吃穿用住,有些来自台湾,有些来自欧洲,或者美国或者墨西哥或者其他任何地方,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去互相理解,我们已经身处全球化的时代了,我们自己也应该是完全全球化的。
现场提问者:你详细地谈到了语境,以及提供语境对美术馆的重要性,以及在展览结束时,观众可以带着有价值的知识离开。但很多策展人认为,语境是说教的。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你和一个这样的策展人合作,他坚信如果提供太多语境、花如此多的口舌去谈背景信息,是填鸭式灌输观众。你作为一个坚持“语境”的艺术家,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Analia:这是个好问题,当我说“语境”的时候,我说的更多的不是那种学究式的信息,我说的“语境”,指的是展览的地点。简单来说,我有些混凝土制的作品,我感觉如果把这些作品放在某个特定的地点,它就可以被解读为艺术;同样的,如果这些作品被放在某个不那么艺术的地方,那可能就是一堆混凝土,这就是我所说的“语境”的延伸之意。并不是什么学究的术语,但我认为这是个好问题,我确实很享受那些真实的“展览”,我走进去,而里面没有任何标签,有时我确实更喜欢如此,因为这会使感官将你引领到理性的反面。
Part4: 艺术生态
收藏家
Damián:这些年来我意识到,策展人和收藏家其实也是艺术家,我们作为艺术家可以计划,可以决定应该做什么,但策展人和收藏家可以决定选择、展示哪个作品,跟随他们自己的梦想和直觉。
Analia:我思考了很多关于艺术家和收藏家的十分微妙的关系,因为一方面你不想做任何与商业有关的东西,想要保持纯粹,希望自己的作品只在美术馆展出,在你看来这是最高荣誉。但另一方面,又很需要他们的支持,否则工作室基本上就要倒闭。你必须妥协你的时间,而这很复杂。此外,我从收藏家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们更了解发生了什么,他们告诉我应该关注谁。收藏,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并且是个很大的工程。我们真的很需要彼此,这样才可以形成一个生态系统,从而生存下来。
画廊
Robin:我们一直在谈论的另一件事是画廊,那么你怎么看你们的画廊?画廊实际上不仅仅是做生意,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文化机构,你们一直在和世界上最好的画廊合作,如何看待他们与私人博物馆或新博物馆合作? 你设想他们最好的支持你的方式是怎么样的呢?
Damián:我想谈一下民族主义,或者民族社群。这很有趣,因为画廊像是成了流动人口。他们的身份认同并非来自国家,而是来自画廊本身。这问题很有趣,因为画廊和某些美术馆,他们有他们特定的客户。反观美术馆,虽然也让人很感兴趣,但其实不是什么好事。我希望美术馆能够对作为个体的艺术家更开放一些,而不是对画廊这样的大型机构。因为几年后,个体艺术家们会开始形成客户关系,而画廊在此时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美术馆如果想收藏什么艺术家的作品,他们需要花更多时间。而对于画廊,这是一种投资,美术馆也应该清楚这点。作为艺术家和机构合作,他们应该有机会得到支持,得到机会,不仅仅是从私人收藏,也应该从公共美术馆那里得到支持和机会。
“Galleries are incredibly important, I mean, galleries, they're pioneers."
——Oscar Murillo
Oscar:画廊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拓荒者。他们是生态系统,他们站在最前线。显然他们支持艺术家,但他们也都是矛盾的,不是吗? 因为在很多方面,他们都是以特定的方式进行交易的。这与信任以及与收藏家的人际关系等等有关,与此同时,他们也承担了支持艺术家思想、制作作品的风险。他们帮助塑造了许多形式、形状、尺寸和特质,我认为他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有趣的时期。也许达米安一直在说这种扩张或是超越国界的画廊,这是一种拥有自己个性的机构,我认为这是一个有趣的微有机组织,就好比画廊展示着来自不同地方和文化的艺术家。我想这就是文化的精髓所在:交叉感染。所以我认为画廊可能是资本主义时期最完美的模型之一。资金是创意所必需的。
“ I think the gallery is perhaps the, one of the very perfect models of the capitalist moment.“
——Oscar Murillo
Robin:作为国际网络,画廊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些机构是扎根的,但也是开放的,甚至连博物馆也不会太国际化,看到美国艺术家出现在上海的大型博物馆或美术馆里,对你来说并不有趣,但他们是给生活在这里的人看的,他们没有机会定期访问MoMA。你们梦想的博物馆是什么样子呢? 它在周遭社会中根植多深?它和跨国家策展人有多少联系?和收藏巨头、画廊,和艺博会又有多少联系呢?
Damián:我真正希望的是,作为一个游客,甚至不作为一个艺术家,对于开放空间的体验。你可以叙述,你可以自由地解释,思考和创造一个空间。虽然对于效率的焦虑反而会让这件事没有效率。它更像是一个冥想,获得想法,探讨和分享的地方。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社区的空间,我认为资本主义并没有经常这么做。而且艺术中发生的事情是很疯狂的,因为如果这样做,如果替代品也成为交换的来源,而这来源从经济上讲就是重要的资金参与,是艺术运营的基础。但我认为最终的原则是在博物馆里创造一个社区,以某种方式来创造一个自由空间。
Part5: 美术馆与社区
本地性与开放性
Robin:理想的博物馆会是一个社区吗?而它又会有多接地气?作为一个艺术家,你想作为社区的一份子探访世界另一边的艺术家吗? 或者你认为应该只待在自己的社区里?
Damián:在我看来,博物馆应该对当地基础有所侧重,因为当你对每一个作品的小细节都严格要求时,也就是当你在这一语境下看到工业的缩影时,这时来看观众的反应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有趣的。我认为,从世界各地搬迁的全球展览,总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语言、形象、政治参考,或者说是文化参考,这都是完全不同的,我认为它应该是当地的,或者说必须是当地的。
Analia: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希望会有这么一个平衡点。
“This is why from the beginning I said I'm not interested in art. I think art is a fraud mostly, and beyond art is culture. And culture is something that exists I think through. I think i's important that it happens through many ways, not simply through art. I think music is probably more successful. And I don't want to assume the art is everything, I'll be lying to you.“
——Oscar Murillo
Oscar:我只是想到身后在那里(油罐艺术中心工地)工作的工人有点难过,因为我从来没有和那些工人发生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真的概括了一切,不是吗?这种新自由主义者和当地居民的观点被抛诸脑后,也许你知道,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这样的。我现在在上海,下周就会去纽约看你们,但最终,很多个体无法拥有那样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从一开始我就说我对艺术不感兴趣,我认为大多数艺术是一个骗局,艺术之外就是文化。我认为文化是存在的,就像是蜜蜂,交叉授粉和人们的相遇,我认为这很重要,这种情况发生在很多方面,不仅仅是通过艺术,我认为音乐可能更成功,我不想假设艺术就是一切,这将是对你们撒谎。
Robin:谢谢各位,我想我要沿着西岸走走,用不同的眼光看看上海的“美术馆大道”,思考我们可以如何改进、重建或为这些机构带去一些什么新的东西。能在一座新的美术馆的建设现场做这次论坛真的很棒,因为我们聊的正是这一话题。再次感谢上海油罐艺术中心团队,谢谢大家!